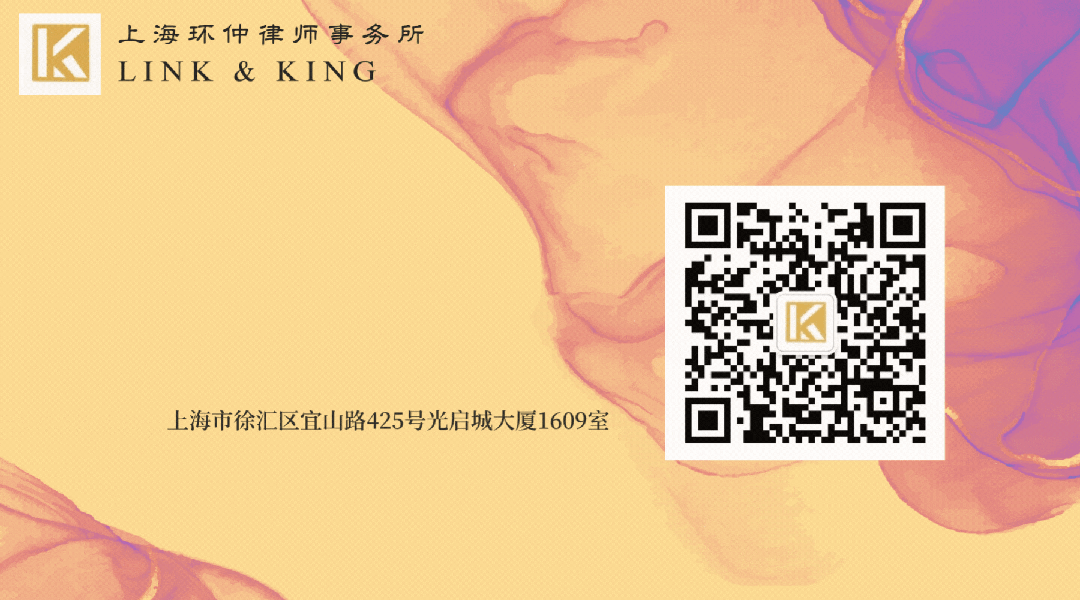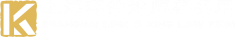环仲视角|公共政策例外与国际仲裁
引言
在全球化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国际商事仲裁凭借高效、灵活等特性,成为解决跨境商业纠纷的关键途径。然而,仲裁裁决在承认与执行阶段并非畅通无阻,“公共政策例外” 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维系国家主权与公共利益的同时,也给仲裁裁决的落地带来了诸多变数。 这一源自国际私法领域的概念,既承载着各国对自身核心价值的捍卫,又在实践中因标准的模糊性,成为争议的焦点。一方面,公共政策例外为各国抵制违背本国基本秩序和公平正义的仲裁裁决,构筑了一道坚固防线;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对公共政策理解的差异,致使这一机制在某些场景下沦为部分国家随意否定仲裁裁决效力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对公共政策例外的深入探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将围绕其理论内涵、司法实践以及适用标准展开论述,并尝试寻找化解困境的方法,旨在为国际仲裁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纽约公约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 纽约公约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是国际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二战后,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际商事纠纷也不断增多。为统一和简化各国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1958 年主持制定了《纽约公约》。 《纽约公约》适用于因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争议而产生且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的国家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以及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不认为是本国裁决的仲裁裁决。公约中规定各缔约国应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国家作出的仲裁裁决,除非存在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情形,如仲裁协议无效、仲裁程序不当、裁决超出仲裁协议范围、裁决违反公共政策等。 《纽约公约》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全球执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提高了仲裁裁决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使得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跨境纠纷的重要方式,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截至 2024 年,已有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公约,使其成为全球最具普遍性和影响力的国际公约之一。 公共政策例外 《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外国法院可基于特定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该条款下,第五条第一款所涉拒绝理由需由被申请人举证,而第二款的理由则由法院主动审查提出。 依据第五条第二款,若申请承认及执行地的主管机关判定:其一,依本国法律,争议事项不能通过仲裁解决;其二,承认与执行裁决违背本国公共政策,便可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这便是本文探讨的公共政策例外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公约》并未对 “公共政策” 作出明确定义,也未指明承认与执行裁决时,应适用国内公共政策原则,还是基于国际公共政策概念的原则。由于公共政策具有开放性的法律属性,各国司法实践对其解释和应用不尽相同。 2002 年,国际法律联盟(ILA)发布了关于 “公共政策” 的建议,该建议被视为反映了最佳国际实践。ILA 将 “国际公共政策” 定义为,一系列获国家认可的原则与规范,其能阻止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或执行 —— 若承认或执行该裁决,将在程序或内容上与之相悖。 ILA 建议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国际公共政策涵盖:一是关乎公正或道德的基本原则,即便国家无直接利害关系,也期望予以保护;二是服务于国家关键政治、社会或经济利益的规则,即 “lois de police” 或 “公共政策规则”;三是国家尊重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义务。需强调的是,ILA 的建议不具法律拘束力。因《纽约公约》未明确公共政策概念,各国在实践中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理解存在差异 。 2 司法实践 案例概述 在Venture Global Engineering v. Satyam Computer Services一案中,Venture Global Engineering(VGE)是一家美国公司,与印度Satyam Computer Services(SCSL)于1999年合资成立Satyam Venture Engineering Services Ltd.(SVES),双方各持股50%。根据双方签署的《股东协议》(SHA),争议需通过仲裁解决,仲裁地设在美国。2005年,SCSL指控VGE因其关联公司破产构成违约,并依据协议条款以账面价值强制收购VGE的股权。VGE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收购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值,双方因此启动仲裁程序。2009年,Satyam爆发震惊全球的财务造假丑闻,其董事长承认虚增10亿美元资产,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案件后续的法律争议,VGE主张Satyam的欺诈行为导致仲裁结果不公,要求撤销裁决。 案例分析 本案的核心争议围绕外国仲裁裁决在印度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展开。VGE援引《1996年印度仲裁与调解法案》第34条,主张即使仲裁地在国外,印度法院仍有权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撤销裁决。其核心论点是,Satyam的财务欺诈行为扭曲了股权估值,严重损害了印度法律的基本诚信原则。Satyam则抗辩称,第34条仅适用于印度国内裁决,而外国裁决应依据《纽约公约》框架处理,且VGE提出异议的时效已过。印度最高法院最终裁定,第34条可扩展适用于外国裁决,并以公共政策为由撤销了仲裁结果。法院对“公共政策”进行了扩张解释,将其定义为包括“违反印度基本政策、国家利益或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一立场突破了传统上对公共政策的狭义理解,强化了司法对国际仲裁的干预权。 此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对欺诈及其与公共政策概念的相互关联作出了更明确的定义,以维护正义为基础,其中也涉及撤销仲裁裁决的补充事实的处理。该案对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印度法院通过扩张解释国内法,开创了以公共政策为由干预《纽约公约》框架下外国裁决的先例,削弱了国际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可执行性,引发国际社会对印度司法环境的担忧。其次,企业实务中需更谨慎设计涉印交易的争议解决条款,例如优先选择新加坡等中立仲裁地,并明确约定《纽约公约》适用条款,以规避印度法院的潜在干预。尽管印度在2021年修订仲裁法以限制公共政策的滥用,但司法实践中类似争议仍频发,显示法律改革尚未完全弥合制度漏洞。 3 公共政策例外的法律适用 各国法律适用现状 普通法系国家普遍对公共政策例外采取狭义解释,仅在最极端情形下适用。例如,美国法院在判例中强调,公共政策抗辩需满足“明显违背最基本的道德与正义”标准,以避免破坏《纽约公约》的统一性。新加坡法院则严格区分程序性公共政策与实体性公共政策,通常仅以程序不公为由拒绝执行裁决,避免审查实体法律适用。 印度长期以广义解释著称,将公共政策延伸至国家经济政策、司法主权等领域。在上述案件中,印度最高法院以“欺诈损害基本诚信”为由撤销外国裁决,引发国际争议。尽管2015年修正案试图限制公共政策范围(如明确欺诈、腐败等具体情形),但实践中仍存在司法扩张倾向,导致国际仲裁终局性受损。 在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48条第6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将公共政策例外限定为“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并建立内部报告制度(需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滥用。例如,在Hemofarm案中,中国法院以仲裁裁决否定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为由拒绝执行,体现了对司法主权的严格保护。 欧盟通过判例法发展出跨国公共政策概念,尤其在竞争法领域,若仲裁裁决违反欧盟反垄断规则(如固定价格协议),成员国法院可直接援引欧盟公共政策拒绝执行。例如,欧洲法院在Eco Swiss案中裁定,欧盟竞争法构成公共政策核心,成员国法院有义务审查裁决是否违反。 存在的问题 《纽约公约》给公共政策例外制度的定义,留下了极大的弹性空间。即便联合国《报告》等文件对公共政策做了进一步阐释,目的也仅在于助力这一例外抗辩制度的应用。这些阐释相对宽泛,主要起引导作用,充分尊重各国在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国际社会之所以 “放任” 公共政策定义的模糊性,一方面是因为在国际层面达成统一认知几乎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由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界定公共政策,更有利于实现《纽约公约》设立该制度的初衷。 不过,各国在公共政策认定的实践上,应做出调整。公共政策在国际层面保持笼统有其合理性,但在各国具体实践中,定义模糊、认识不一带来的弊端远超益处。以我国为例,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执法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这些因素可能加剧上述弊端。在立法环节,公共政策的法律术语、范围和判断标准缺乏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公共政策的表述、认知存在差异,审查标准不统一,推理过程简单化,这些都凸显出地方法院在界定公共政策标准时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不仅阻碍公共政策例外制度发挥积极作用,还会让民众误以为公共政策可以随意使用,从而造成滥用。但滥用公共政策并不能达到民众预期效果,反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反思与改进方向 在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里,公共政策条款既需要确定性,也离不开灵活性。明确公共政策的具体内容与适用范围,对构建可预测、可信赖的国际商事法律环境至关重要。而要实现公共政策的确定性,不仅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仲裁机构、仲裁员、国际组织和研究者多方协作,还依赖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增进相互理解与融合的大环境。 与此同时,公共政策条款的灵活性同样不可或缺。这既能弥补法律与生俱来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帮助其应对难以预见的状况,满足新兴社会需求,也能够广泛囊括随时间和文化背景不断变化的社会与法律价值观。 不过,公共政策的灵活性利弊并存。一方面,它赋予法院必要的自由裁量空间,用以处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案件;但另一方面,部分法域的法院可能会借此 “不恰当” 地对争议实体问题进行过度审查 。 环仲国际业务团队 袁杜娟 环仲高级法律顾问 商舒 环仲高级法律顾问 陈珏 合伙人 扶怡 环仲高级法律顾问 涉商事纠纷相关业务咨询请点击阅读原文,直达环仲官网,或电话咨询:13127864609,邮箱咨询:link-king@linkarb.com.cn 本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资讯或文章仅为交流讨论目的,不代表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法律意见。任何依据本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作出的判断或决定(无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您需要相关法律意见或法律服务,欢迎与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联系。 点击“阅读原文”可访问律所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