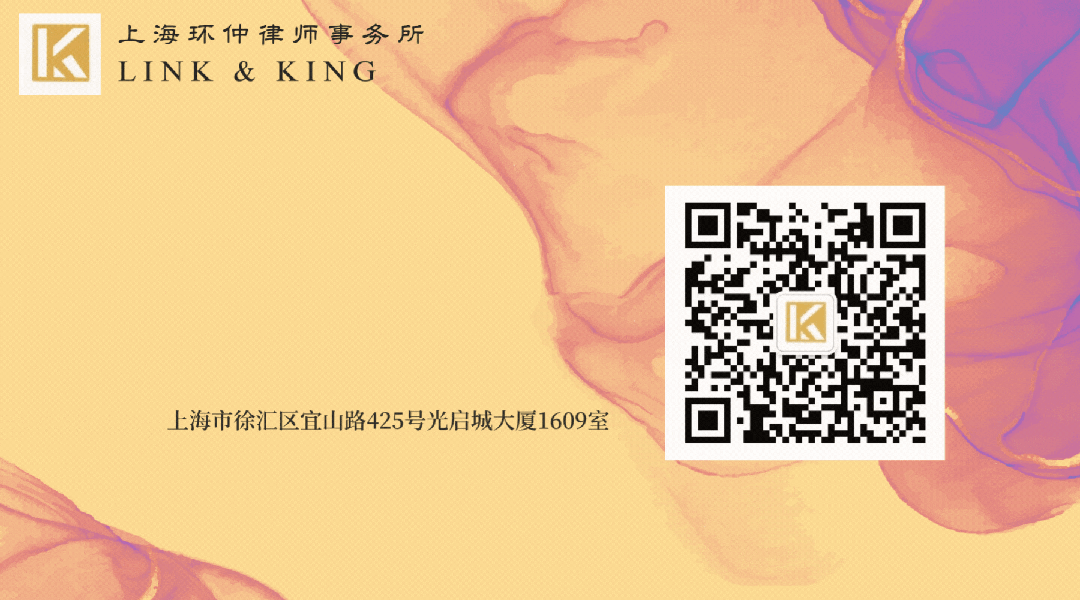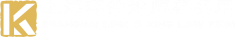仲裁地、审理地、仲裁机构所在地概念辨析
引言
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仲裁地(seat of arbitration)、审理地(place of hearing)与仲裁机构所在地(location of arbitral institution)的混淆常引发法律争议与执行障碍。这类争议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仲裁法》未对三者作出明确定义,导致司法实践中常以“仲裁机构所在地”替代“仲裁地”,甚至将“审理地”与“仲裁地”混为一谈,这不仅违背国际通行规则,还可能削弱仲裁裁决的确定性与跨境执行力。 从全球视角看,仲裁地的法律意义早已超越物理空间,成为决定裁决国籍、程序法适用及司法监督权的核心而审理地仅为程序便利的物理选择,与法律效力无关;仲裁机构所在地则更多体现机构注册属性,三者分属不同维度 这种混淆不仅导致仲裁协议效力争议频发,还可能因仲裁籍属认定分歧而影响《纽约公约》框架下的裁决承认与执行。 当前,中国《仲裁法》修订草案拟增设“仲裁地”制度,标志着立法层面对国际规则的主动接轨。在此背景下,厘清三者的法律边界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是提升中国仲裁国际化公信力的关键一步。本文旨在通过学理分析与案例解构,为构建清晰的概念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1 概念辨析 仲裁地(Seat of Arbitration) 仲裁地(seat of arbitration或place of arbitration)通常指法律意义上仲裁进行的地点。在现代仲裁实践中,仲裁地完全是一个法律概念,可以由当事人通过协议约定,或根据仲裁规则或相关法律确定,并不一定是仲裁程序实际进行的地点。比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 20 (1) 条明确:“当事人可自主约定仲裁地点。若未达成约定,仲裁庭需结合案件状况,包括当事人的便利条件,来确定仲裁地点” 。该示范法的此项规定,与众多主要国家的立法相符。像韩国 2002 年《仲裁法》第 21 条 1 款、德国 1998 年《仲裁法》第 1043 条 2 款、瑞士《国内仲裁法》第 355 条 3 款以及《国际仲裁法》第 176 条第 3 款,还有英国 1996 年《仲裁法》第 3 条,都有相似条款。 仲裁地连接国际仲裁和国内法院,为国内法院支持和监管国际仲裁提供法律连接点。仲裁地通常带来两个法律效果:一是仲裁活动受到仲裁地法律管理,二是仲裁裁决的作出地为仲裁地。 审理地(Place of Hearing) 开庭地并非法定术语,一般指仲裁庭审程序实际开展的地方,它可能和仲裁地相同,也可能在仲裁地以外。《仲裁示范法》以及主要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都准许当事人自行商定开庭地,或者由仲裁庭自主确定,不管其与仲裁地是否一致。 《仲裁示范法》第 20 (2) 条表明:“为方便仲裁庭成员协商、听取证人、专家或当事人陈述,抑或是检查货物、其他财产或文件,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能够在其觉得合适的任意地点进行会晤。” 与之相仿,《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 18 (2) 条规定:“经与各方当事人沟通,仲裁庭可在其认为适宜的任何地点开庭和举行会议,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除外。” 上述仲裁地与开庭地能够不一致的规则,也获得了许多主要国家立法的认可。比如英国 1996 年《仲裁法》第 34 条第 2 款 a 项、瑞士《民事诉讼法》第 355 条第 4 款、德国 1998 年《仲裁法》1043 条第 2 款、韩国 2002 年《仲裁法》第 21 条第(3)款都有相关规定 。 仲裁机构所在地(Location of Arbitral Institution) 仲裁机构所在地,是在当事人未就仲裁地点达成一致时,用于判定仲裁国籍的一个依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8 条将 “仲裁机构所在地” 与 “仲裁地” 并列列出,这意味着在我国法律环境中,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判定优先于仲裁地。仲裁机构所在地是我国立法的特别设定,它指的是处理商事仲裁的机构所在的国家、地区,以及该机构所处的法律框架或体系,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针对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国籍认定给出的解答。 仲裁机构通常设有固定办公场地,其所在地可依据仲裁机构的地理位置来明确。一旦当事人认可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仲裁地点,如果没有另行约定,就表明同意采用仲裁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来解决仲裁纠纷 。 2 案例分析 案例概述 2009年5月,某机械公司与瑞典某科技公司签订《U型管购货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合同中仲裁条款约定,因合同引起的任何争议应交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以下简称ICC仲裁院)根据其仲裁规则由1个或多个指定仲裁人员作出最终裁决,仲裁地为中国北京。2019年4月,某机械公司依据涉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以瑞典某科技公司为仲裁被申请人,向ICC仲裁院提起仲裁,ICC仲裁院予以受理。在该案中,瑞典某科技公司提起了仲裁反请求。仲裁期间,仲裁员曾就争议程序安排及处理作出《第1号程序令》《第1号程序时间表》《第3号程序令》《第4号程序令》等,准予了瑞典某科技公司延期60天提交证人证言,并在嗣后驳回了某机械公司关于延长两周提交回复证人证言时间的申请及逾期提交的额外文件披露申请。 2021年2月,ICC仲裁院就该案作出仲裁裁决。2021年9月,某机械公司以涉案仲裁裁决仲裁程序违法为由,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理由主要为,独任仲裁员和瑞典某科技公司违反《第1号程序令》和《第1号程序时间表》等,反复提交新证据,未给予某机械公司足够的机会进行质证,剥夺了其程序利益;独任仲裁员在处理程序问题时区别对待双方当事人,有失中立性和公正性,严重违反了《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独任仲裁员在仲裁期间未履行披露义务,其与瑞典某科技公司的律师存在私人朋友关系,多次参加同一会议,且为该律师参与撰写的书籍发表书评。瑞典某科技公司提交仲裁庭审笔录,证明某机械公司在仲裁庭审即将结束前发言,称“本案仲裁程序系按照规则进行,显示了国际仲裁的最佳实践”;瑞典某科技公司另提交邮件及声明,证明仲裁结束后半年左右,《亚洲争议评论》邀请仲裁员撰写书评,瑞典某科技公司代理人并未参与该过程,只是事后应《亚洲争议评论》的要求,给《亚洲争议评论》提供了一本赠阅本。双方当事人在主张及答辩独任仲裁员是否履行了披露义务时,均引用了《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的有关规定。 北京四中院认为,涉案仲裁裁决属于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所作的仲裁裁决,应当视为中国涉外仲裁裁决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某机械公司有关该案仲裁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遂驳回了某机械公司的申请。 案例分析 本案系国内首例申请撤销境外仲裁机构以我国内地为仲裁地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也是明确当事人在仲裁中共同选择适用的国际商事仲裁“软法”在我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中的地位及适用的首案,在我国仲裁司法审查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多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多按照“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来确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属性,将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为境外仲裁裁决,以往该类裁决在我国内地只能进入申请承认(认可)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程序。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明确境外仲裁机构以我国内地为仲裁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视为我国内地的涉外仲裁裁决,以“仲裁地”标准确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属性。本案正是在该纪要出台之前受理,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我国有关涉外仲裁的法律规定对此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尊重当事人选择和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立足点,也彰显了我国司法接受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发挥作用的开放姿态。 同时,对仲裁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予以审查时,除适用我国涉外仲裁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境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外,本案中首次明确,法院可以适用当事人双方选择或者一致引用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等国际商事仲裁“软法”。国际商事仲裁“软法”,是由一些国际组织和仲裁机构针对国际商事仲裁中容易产生冲突和分歧的程序法律空白所制定的,其虽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和实际效果,在实践中通过当事人的约定或是仲裁庭的选择等方式在具体案件中予以适用或者作为参考,在协调法系差异、填补法规制度空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方面,本案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本案的妥善裁判,对今后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3 我国相关立法的转变 2023年9月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304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需要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当事人可以向申请人住所地或 者与裁决的纠纷有适当联系的地点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此条款将需要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非国内裁决,从此前的“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修改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经此修改后,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境外仲裁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将被认定为非国内/境内仲裁裁决,此条的修改亦可以视为对我国仲裁裁决籍属趋向以仲裁地为标准的一个体现。 此前我国仲裁法亦无仲裁地概念。2024年11月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草案)》,是现行仲裁法自1995年施行以来的一次重要修订。《仲裁法》修订草案第78条引入了仲裁地概念,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仲裁地,作为仲裁程序的适用法及司法管辖法院的确定依据。……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仲裁规则规定的地点为仲裁地;仲裁规则没有规定的,由仲裁庭按照便利争议解决的原则确定仲裁地。” 该条明确了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表明《仲裁法》修订意见稿将以仲裁地作为仲裁籍属的认定标准。 环仲国际业务团队 袁杜娟 环仲高级法律顾问 商舒 环仲高级法律顾问 陈珏 合伙人 扶怡 环仲高级法律顾问 涉商事纠纷相关业务咨询请点击阅读原文,直达环仲官网,或电话咨询:13127864609,邮箱咨询:link-king@linkarb.com.cn 本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资讯或文章仅为交流讨论目的,不代表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法律意见。任何依据本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作出的判断或决定(无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您需要相关法律意见或法律服务,欢迎与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联系。 点击“阅读原文”可访问律所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