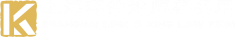我国“以房养老”四大纠纷类型及其争议焦点与裁判思路之赠予定性纠纷

刘英明
环仲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引言
前中国一部分养老资金存在缺口但又有独立产权住房的老人希望能够实现“以房养老”。关于“以房养老”形式,目前政府提及最多的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但是,这一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业务形式,在中国当前却开展的不够普遍和成熟。当前现实生活中,中国民众实施“以房养老”的方式具有多种样态。
本系列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案例的方式归纳“以房养老”的类型、发掘其实务争点,总结其风险防范要点,以期有助于有需求的老年人明白各种方式的优缺点,各种方式的风险关键点,从而能理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以房养老”方式,并在律师的帮助下通过清晰约定或其他法律安排规避风险。本篇文章主要介绍以房养老之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中的赠予定性纠纷。
1
背景介绍
“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中央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作了专门部署。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需求,即部分老人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入住养老机构或购买其他养老服务,而他在城市拥有独立产权住房,他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将产权住房的部分权利或价值让渡出去,从而获得部分收益以贴补自己的养老资金缺口。质言之,即部分养老资金存在缺口但又有独立产权住房的老人希望能够实现“以房养老”。关于“以房养老”形式,目前政府提及最多的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但是,这一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业务形式,在中国当前却开展的不够普遍和成熟。当前现实生活中,中国民众实施“以房养老”的方式具有多种样态。本文尝试通过系统梳理案例的方式归纳“以房养老”的类型、发掘其实务争点,总结其风险防范要点,以期有助于有需求的老年人明白各种方式的优缺点,各种方式的风险关键点,从而能理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以房养老”方式,并在律师的帮助下通过清晰约定或其他法律安排规避风险。
2023年8月初,笔者通过“威科先行·法律信息数据库”,以“以房养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一共收集到883篇相关裁判文书。然后,笔者对这883篇案例逐一进行阅读整理,寻找重要争点与“以房养老”直接相关的裁判文书,剔除重要争点与“以房养老”关联不大的裁判文书。这样整理下来,一共剩下118份重要争点与“以房养老”直接相关的裁判文书。进一步归类、挖掘,我们发现这118份裁判文书大致可以分为以房养老之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以房养老之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继承纠纷、以房养老之抵押借款转投资纠纷、以房养老之卖房与租房等纠纷这四大类。每大类纠纷又可以进一步切分成四到五个二级问题。
2
以房养老之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
就笔者所搜集的118件以房养老法律纠纷而言,其中36件纠纷主要与赠与合同、特别是附义务赠与合同有关。这些纠纷根据其争议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小类。依次展开如下:
赠与定性纠纷:名为买卖,实为赠与
这类争议案例一共有3件。试列两份典型判决意见如下:
案例1,39XX与XX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本案一审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还是赠与关系。区分买卖和赠与的关键在于买卖合同是有偿合同,买受人应为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支付对价;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赠与人无偿给付财产,受赠人不负担相应对价。原告基于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主张双方系房屋买卖关系,但该买卖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明显有异于正常的房屋买卖合同:其一,买卖合同除约定了转让价格和过户时间外,其余主要条款包括付款方式、交房时间、违约责任等均为空白;其二,原、被告在办理过户手续时被告未支付任何房款,亦未办理房屋贷款,而原告仍将系争房屋过户至两被告名下;其三,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系争房屋已过户给被告,并由两被告居住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原告曾向被告催讨过房款。直至诉讼前几日,原告才向被告发函催讨房款。虽然原告申请了证人翁根龙、翁红妹出庭作证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催讨房款,但两位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且两位证人均未亲自参与原、被告对系争房屋的处理过程,其陈述内容为事后听说,系传来证据。故XX、XX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上述有异于正常房屋买卖的情形,原告仅以双方是亲属关系予以辩解,但该辩解明显缺乏说服力。而被告主张的双方实为赠与,签订买卖合同是为了办理过户时少缴税费,且被告承诺让两原告居住至终老的意见,正好能够合理解释为何双方对于买卖合同约定的房价款是否实际支付并不关心。原、被告签订买卖合同及转移产权的目的并非以支付对价为前提,故原、被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房屋赠与。现赠与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以被告未支付房款为由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及恢复产权至原告名下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2,高某2诉T赠与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一审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对房屋买卖合同(包括双方已经签字的网签合同)的效力及履行存在争议,经审查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赠与等其他法律行为的,应根据隐藏法律行为的性质进行处理。本案中,高某2与被告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依照常理,双方之间应当存有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及相应的履行行为。但结合查明的事实发现,高某2与被告及案外人高某1之间一系列的外在行为与上述意思表示存在相悖之处,具体如下:其一,被告表示涉案房屋系其母娄某某与原告高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2003年娄某某去世,按照被告的陈述,其因继承母亲遗产已成为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之一;2008年高某2立下遗嘱,表示愿将房屋留给被告及高某1继承;2011年7月29日即《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次日,被告又与妹妹高某1自愿签署《房屋共有协议》,约定两人各占房屋50%份额,在上述情形下,被告缺乏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主观动机。其二,从《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内容分析,其中虽然约定了房屋的价格,但该价格甚至低于高某2在2005年购买涉案房屋的价格,且合同对于房屋交付时间、产权转移、违约责任、付款方式和期限等重要条款均未明确,且未有证据显示被告向高某2支付过购房款。在未收到任何房款的前提下,高某2就把房屋过户到被告名下,被告甚至与妹妹约定房屋在父亲有生之年由父亲居住使用,父亲故去后姊妹二人及配偶、子女居住涉案房屋亦有限制条件,上述情形与房屋买卖的交易惯例不符,亦与购房人支付对价购买房屋的合同目的相悖。其三,被告主张全部房款均由其承担与支付,但又在合同签订次日与妹妹签署协议约定房屋由二人平等享有所有权及处分权,显然与常理不符。而高某2对于《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原因从便于过户、减少支出等方面作出了合理解释。故此,结合上述分析及高某1的《关于同意父亲高某2收回房子产权决定的声明》,本院认为高某2和被告之间形成的是赠与合同法律关系。”
本文作者
刘英明,环仲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现任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曾任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副处长。现任上海市律协民商事诉讼研究委员会委员、全国省级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咨询专家、曾任某直辖市法官入额遴选笔试试题主要命题人多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移投行专家智库高级研究员、宁波仲裁委仲裁员、南昌仲裁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青浦区法学会常务理事等。在公司治理与并购重组领域民商事诉讼及刑事辩护领域有丰富执业经验。
环仲跨境家事团队

汪峻岭 Joseph Wang
律师/合伙人
电话:13601626815
邮箱:Joseph.wang@ linkarb.com.cn

刘英明 Yingming Liu
律师/合伙人
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电话:13816936691
邮箱:yingming_liu@linkarb.com.cn

田云云 Monica Tian
律师
电话:13512119329
邮箱:monica.tian@linkarb.com.cn

高灵芝 Gemma
律师
电话:15822250911
邮箱:glzshuiel@163.com
本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资讯或文章仅为交流讨论目的,不代表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法律意见。任何依据本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作出的判断或决定(无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您需要相关法律意见或法律服务,欢迎与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