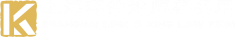环仲视角|中美技术脱钩中的出口管制境外管辖分析(中)
出口对一国贸易平衡意义重大,既能减少贸易逆差,又能创造外汇收入。而出口管制,从历史来看,政治因素往往重于经济因素,旨在推动一系列政策,和平时期多针对军事及高科技产品。冷战时美国设立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COCOM),后被强调透明度与非扩散的《瓦森纳协议》替代。疫情之下,单边出口控制政策复苏,美国对先进技术产品实施的域外出口控制尤为突出,将中国视为对手,对涉华相关外国活动加强管控。
本系列文章基于中美技术脱钩背景,深入剖析美国出口管制单边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美国出口管制法在境外适用的成本与可取性,运用地缘经济贸易理论探讨平衡联合安全成本与规范收益。本篇文章继续分析美国如何应用地缘经济贸易理论来平衡联合安全成本和规范收益。
一、地缘经济贸易法下的出口管制治外法权
(一)出口管制域外效力的政治成本
境外出口管制相关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与第三国的关系受到压力,这些第三国是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源自美国。事实上,看似对原产于美国的商品的转口,可能更应归类为对本地制造的产品出口,这些产品恰好包含某些进口的组件或软件。对于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或涉及某些美国人参与的外国产品,也存在类似的认知差异。
美国限制此类交易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激怒受影响的外国人民和政府。第三国政府往往认为境外出口管制是对其领土主权的不合理干涉,从而违反了基于主权的国际法。当美国的贸易伙伴选择对其领土内的商品和人员行使绝对管辖权,且这种方式与美国对商品或技术再出口所设定的条件相冲突时,实质性的法律冲突就会产生,并很容易升级为民族自豪感的问题。
与域外出口管制相关的政治紧张局势不仅消耗了寻求解决方案的几个主权国家不成比例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还干扰了美国和外国政府在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的能力。在新自由主义贸易秩序下,当各国大多试图使经济收益最大化时,很少有情况值得承担这些成本。
(二)出口管制域外效力的经济成本
与政治成本相比,经济代价更易量化。域外出口管制抑制了第三国的出口,从而减少了外汇收入,并间接限制了许多跨国公司的生产、就业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即使出口管制的外国法管辖权并非仅仅通过迫使参与者接受美国法律来直接禁止海外交易,它也会给此类交易带来额外的成本。
出口管制的外国法管辖权增加了所有潜在外国买家购买美国原产商品以及含有美国原产技术或软件的外国原产商品的成本。这使得许多外国公司面临有限的选择——要么筛选客户以剔除中国客户,要么筛选需要单独许可证的交易,要么筛选涉及受管制美国人的交易,甚至停止从美国进口某些高科技产品。在这种时期,实施出口治外法往往为外国公司生产所需商品创造了相应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出口管制似乎刺激了国外新产能的增长,外国卖家取代了美国出口商曾经占据的市场份额。
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对于那些位于价值链中间、不必依赖美国高端芯片的企业来说,它们可能会选择从其他国家不限制此类技术贸易的芯片制造商购买产品。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在当前的实体名单下,如果美国继续实施这些限制,美国半导体公司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可能会失去8个百分点的全球市场份额和16%的销售额。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其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美国公司可能会在同一时期失去18个百分点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
美国的出口禁令也推动了中国芯片自给自足的进程。在中国最近的五次年度计划,中国政府承诺到2025年将再向高科技产业投资1.4万亿美元,支持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这些自给自足的计划和技术补贴可以说有助于中国在长期内获得技术领先地位。
总之,域外贸易管制的经济成本会对美国企业的出口和技术、美国公司外国子公司的运营、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美国的总体经济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二、重新评估出口管制的域外效力
——从地缘经济视角出发
(一)地缘经济视角下出口管制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出口管制的治外法权仍然带来了高昂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由于担心中国增加相应的治外法权规定,这些规则深深侵犯了美国贸易伙伴的监管权力。然而,在安全导向型决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安西娅・罗伯茨主张,重新评估各国对经济和安全的不断变化的看法,有助于预测个别国家的战略偏好。
在新兴的 “地缘经济国际秩序” 下,各国不再仅仅优先考虑自身经济收益,而是更加倾向于那些不会威胁自身安全的战略贸易伙伴的经济收益。从这种地缘经济视角来看,美国近期出口管制扩张的国际接受表明,超领土的出口管制可以产生积极的外部性。
地缘经济秩序与出口管制和出口管辖权直接相关。例如,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崛起及其军民融合的终端用途目标被视为对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全球半导体设计和设备制造的安全威胁。考虑到美国芯片行业在设计方面的垄断地位,实施出口管制导致美国芯片设计和中小企业的全球销售能力下降,增加了海外制造公司,包括中国、韩国和台湾公司在内的成本。
(二)各国在出口管制下的合作与权衡
这些经济损失可能超过其他地区设计和设备公司的收益,只有通过安全收益才能弥补。这促使美国盟友继续合作,不反对美国法律的域外适用。如果美国的动机主要是经济而非政治,其贸易伙伴在经济上的妥协可能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失败,导致更多的不信任和不合作。
国际法中,放弃一定程度的主权以换取更大的执法权力是多边秩序的基石,并在当代地缘政治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大多数美国的亲密贸易伙伴愿意将其国际贸易决策与美国的战略关切相结合,而非提出管辖权异议。例如,美国、荷兰和日本已达成协议,共同协调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这些国家要么缺乏设计精巧、覆盖广泛的出口管制制度,要么没有资源进行昂贵的管制。它们可能更愿意放弃某些管辖权主张,以换取来自美国的贸易或投资激励。为促进可持续合作并弥补监管过度,美国也愿意放弃某些短期经济利益,为其贸易伙伴提供额外政策激励,包括经济和安全利益。
如果美国的出口管制所产生的负面外部性能被更紧密的安全合作带来的好处所部分弥补,美国就更容易说服其最紧密的贸易伙伴接受更大的司法管辖权。作为回应,美国盟友可以援引美国法律中的条款,以避免进一步得罪中国。
三、执法协调的新侧重点
(一)出口许可证豁免制度
出口许可证豁免或自动许可出口(APR)是一种授权,允许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出口、转口或国内转让本应需要许可证的受《出口管理条例》(EAR)管制的物品。这一授权允许在符合这些外国出口管制法律的情况下,从某些国家进行无许可证的转口。为了减少与盟国管辖权的冲突,一些拟议的《出口管理条例》规则变更正在进行中。
具体而言,第740.20(e)条提议取消对某些国家之间再出口许可例外STA出口、再出口或国内转移的物品使用再出口许可例外APR的限制。这些国家与美国在出口管制方面密切合作,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确保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实施再出口管制。因此,鉴于这些国家设计了类似的军民两用出口管制系统,并利用这些系统推进共同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工业与安全局(BIS)认为有必要给予这些国家更宽松的待遇,允许其接收根据APR获得的物品。
此外,美国工业与安全局还为前沿半导体许可证新增了针对受外国竞争的产品的审批审查政策假定,以及为总部位于不太敏感地区的公司从事的中小企业和中高端计算活动新增了两项新的临时通用许可证(TGL)。这些措施为国内和美国盟友的半导体供应商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旨在更有效地维护美国的长期国家安全。
加强确保美国盟友维持并执行与美国相同的高标准许可政策和出口限制,有助于美国更容易协调执法决定,从而减少美国法律在海外应用的负担。向专制政权转移敏感的国家安全相关技术是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共同关心的问题,许多盟友将从这些提议的变革中受益。
(二)美国公民管控的例外
此外,考虑到盟友的利益,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对旨在确保美国公民和公司不能为中国先进半导体制造提供支持的“美国公民管控” 进行了重大修改。这些重要的排除条款大大缩小了美国个人活动的范围。
首先,BIS将那些受雇于或代表总部位于美国或盟友国家、且不受中国或美国武器禁运国家控制的公司工作的美国个人排除在外。这一调整与之前的规定存在重大差异,缓解了行业对于雇佣和吸引美国员工的困难的担忧。
其次,BIS将为不生产先进芯片的设施提供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美国个人排除在外,以避免过度限制他们参与传统芯片生产的能力。这些出口限制旨在不削弱美国个人为总部位于美国和盟友国家的公司工作的能力,同时实现其安全目的。
为了进一步调整这些新的限制措施并尽量减少管辖权冲突,BIS正在实施新的许可例外。总体而言,这些例外是针对特定情况的豁免,而非系统性的调整,但它们能够有效安抚美国盟友,并支持美国现有的广泛出口管制管辖权,以实现共同的安全目标。
尽管如此,美国出口管制治外法权仍依赖执法自由裁量权。尽管在地缘经济贸易法范式下,这种治外法权的益处已显著增加,但与在盟友国家之间更好地界定国家出口管制法的可接受治外法权应用的规则相比,执法协调更像是一种专注于最终收益的实用捷径。
本文英文原文为《Mapping Export Control Extra-erritoriality in the US-China Technology Decoupling》,发表于《Journal of World Trade》58卷第4期。
参考资料及数据来源
[1]D. Rosenthal & W. Knighton, Natio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11 (Chatham House Papers No. 17 1982).
[2]Antonio Varas & Raj Varadarajan, 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9 Mar. 2020), https://www.bcg.com/en-au/publications/2020/restricting-trade-withchina-could-end-united-states-semiconductor-leadership (accessed12 May 2024).
[3]Pengfei Han, Wei Jiang & Danqing Mei, Mapping U.S.-China Technology Decoupling: Policies,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cience, 1-28 (2024), https://doi.org/10.1287/ mnsc.2022.02057.
[4]Austen Parrish,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traterritoriality, Sovereign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Standards and Sovereigns: Legal Histories of Extraterritoriality (Routledge 2019), at 3.
[5]C. Gregory, Allen Emily Benson & Margot Putnam,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Announce Plans for New Export Controls on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Apr.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japan-and-netherlands-announce-plans-new-export-controlssemiconductor-equipment#:~:text=In%20January%202023%2C%20the%20United,advanced%20semi conductor%20equipment%20export%20controls (accessed 12 May 2024).
[6]Public Information on Export Controls Imposed on Advanced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tem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2022 and 2023,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17 Oct. 2023),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policy-guidance/advanced-computing-and-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items-controls-to-prc (accessed 12 May 2024).
本文作者
商舒,环仲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执业律师。曾担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调解和在线争议解决部门负责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英美法项目主要负责人;发表过多篇英文学术论文,在美国国际法学会、硅谷仲裁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任职,同时在中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仲裁委员会电子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电子仲裁中心、美国国家仲裁中心等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有丰富的仲裁经验。
本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资讯或文章仅为交流讨论目的,不代表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法律意见。任何依据本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作出的判断或决定(无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您需要相关法律意见或法律服务,欢迎与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