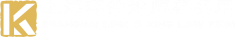环仲视角|中美技术脱钩中的出口管制境外管辖分析(上)
引言
出口对一国贸易平衡意义重大,既能减少贸易逆差,又能创造外汇收入。而出口管制,从历史来看,政治因素往往重于经济因素,旨在推动一系列政策,和平时期多针对军事及高科技产品。冷战时美国设立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COCOM),后被强调透明度与非扩散的《瓦森纳协议》替代。疫情之下,单边出口控制政策复苏,美国对先进技术产品实施的域外出口控制尤为突出,将中国视为对手,对涉华相关外国活动加强管控。
本系列文章基于中美技术脱钩背景,深入剖析美国出口管制单边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美国出口管制法在境外适用的成本与可取性,运用地缘经济贸易理论探讨平衡联合安全成本与规范收益。本篇文章将从出口管制政策的历史与现状入手,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一复杂议题。
一、美国出口管制安全化:以最终用途为重
(一)早期出口管制法规与架构
1949 年,美国出台《出口控制法》(ECA),建立起一种重新定向制度,其核心目的是维持战略重要商品在美国国内市场的充足供应,以保障国家在关键物资方面的需求,这一举措为后续出口管制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 1979 年,《出口管理法》(EAA)颁布,将美国的贸易限制举措整合进一个全面的出口管制框架之中。从立法背景可以看出,美国国会期望该法案能够对源自美国的商品和技术在跨国层面进行有效管控。与《出口管理法》紧密相关的《出口管理条例》(EAR),其主要关注点聚焦于出口商品、软件以及技术的身份认定和来源追溯。
依据瓦森纳协定,美国工业与安全局(BIS)制定并维持着一套分类方案,即《商业管制清单》(CCL)。这份清单详细罗列了各类可能对美国出口管制产生影响的商品、软件和技术。按照清单对物品的分类,一旦向外国目的地出口相关物品,根据其类别,可能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对于那些被明确要求具备出口许可证的物品而言,在未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获得单独许可的情况下,严禁进行转口出口。通过这一系列规定和操作,美国得以对完全在美国境外制造、但却是源自美国技术的直接产品行使管辖权,这些产品均受到《商业管制清单》的严格约束 。
然而,在近几十年间,美国出口管制的有效性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这一现象主要归结于两个关键因素。
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产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这一趋势使得美国原本直接的出口管制措施在防止敏感技术外流方面的效果大打折扣。因为敏感技术往往不再是从美国直接流向令人担忧的目的地,而是通常会经过多个中间国家进行出口和再加工,最终才抵达目标地,这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监管的难度。
另一方面,针对传统瓦森纳协定之外,那些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而有意监管的特定敏感技术,难以实施有效的管控。由于清单的局限性以及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新兴的敏感技术未能及时、全面地被纳入监管范围,导致监管存在漏洞。
为应对出口管制有效性下降的问题,2018 年,特朗普政府颁布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该法案明确赋予政府通过制定出口管制规则来保障 “国家安全” 以及推进 “外交政策” 的权力。在这一法案中,“国家安全” 的概念被进一步拓展,指 “在科学、技术、工程和制造业领域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涵盖了 “对创新至关重要的基础技术” 。通过这种对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大解释,同时减少其与国际防扩散风险的直接联系,《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为美国基于自身对国家安全重点的评估,在更广泛的技术领域内继续实施单边出口管制措施提供了所谓的正当理由。
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新将供应链安全纳入美国出口管制架构的重要部分。这一转变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新兴技术若被用于非法用途,可能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引发基于安全性的中断,对美国乃至全球的供应链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供应链安全与公平劳动实践、可持续采购以及避免在侵犯人权行为中同谋等其他国际法原则紧密相连。基于此,美国的监管重点逐渐转向另外两种类型的出口管制方式,即最终用户控制或受关注实体控制。根据新的规定,不在 EAR或CCL 清单上列出的物品,除非它们被出口到受美国贸易禁运的目的地,或者其 “最终用户” 或 “最终用途” 被认定为不可取,否则不需要美国出口管制许可证。BIS 通过发布 “最终用户” 或实体名单,向出口商提示一些可能参与扩散活动的组织和公司;而 “最终用途” 控制则直接针对涉及未列物品和未列最终用户的特定关注个人或公司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能够通过灵活定义最终用户或最终用途,轻易地对涉及美国技术的外国交易行使监管权力。这种以最终用途 / 最终用户为重点的管制模式,对美国出口管制的管辖范围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最终用途 / 最终用户管制的有效性与管辖范围的广度直接相关。
二、美国出口管制境外管辖权的扩张
基于最终用途 / 最终用户的分类方式,《出口管制条例》(ECRA)和《出口管理条例》(EAR)均纳入了域外管辖条款,使得在美国境外生产的物品也受到其管辖。在最近修订的条款中,有两种类型格外引人关注。
《出口管理条例》第 734.9 条规定了 “外国生产产品”(FDP)规则,明确指出 “位于美国以外的外国生产的物品” 如果是某些美国技术或软件的 “直接产品”,则可能受到《出口管理条例》的管制。2020 年 5 月,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一项临时规则,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进行修改,旨在限制基于华为设计的某些外国产品向中国的华为进行出口、再出口或转让。尽管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中并未直接提及华为,但新规则在实体名单中新增了一个脚注,专门针对华为实施限制。到了 2022 年,美国工业与安全局进一步扩大了实体名单中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再次强化对华为的限制,使得基于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无论其位于世界何处,其再出口和转让都受到直接控制。并且,这一实体名单 FDP 规则同样适用于之后被添加到实体名单的其他实体。
此外,美国将更多中国实体添加到 “未验证名单(UVL)”,借此能够对涉嫌参与先进计算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活动的中国实体施加 FDP 规则。根据最新修订的实体名单 FDP 规则,一旦已知外国生产的物品将用于或被订购给与华为相关的实体,就需要重新申请出口许可证。这些规则的实施,迫使依赖美国技术来源的第三国供应商,即便与华为仅存在某种间接关联,也不得不停止向华为及其他众多中国客户销售产品。
另一项新规定即 “超级计算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涵盖了特定受出口管理条例管制的直接产品,其中包括在外国生产的半导体、计算机、电信或加密技术、软件或设备等。该规则要求,任何受美国出口管制的产品,只要是用于中国或运往中国的超级计算机,都必须获得再出口或转让许可证。这些明确的域外限制条款,极大地扩大了美国出口管制法的管辖范围。尤其在半导体行业,这些规则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不仅直接禁止中国终端用户获取最先进的芯片,还禁止通过第三国向中国销售半导体制造设备(SME),同时限制第三国向中国终端用户销售使用这些 SME 生产的芯片。此外,这些规则还明确表明,如果 “外国政府的行动” 阻碍 BIS 做出合规决定,那么外国公司获取美国技术将受到负面影响。
美国在出口管制方面的管辖权扩张不断升级。自 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修订后,开始通过规范美国公民在特定国家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或开发的活动来主张治外法权。依据《出口管理条例》第 744.6 条,BIS要求所有美国公民,若直接或间接支持中国开发或生产先进节点半导体所需活动,都必须获得许可,即便所生产物品不受《出口管理条例》管制,该规定依然适用。
这项新要求,其影响范围远超以往美国制裁法涵盖的活动范畴。该法律赋予商务部权力,监管美国公民在全球任何地方提供外国军事情报服务的活动,实际上禁止美国公民在生产新兴技术的实体工作,或向外国公民发布相关技术信息 。
美国试图借涉及美国原产技术、软件或相关人员,对与部分中国终端用户的出口交易施加广泛限制,虽试图以主动人格原则或保护原则为对美国公民的出口管辖权扩张辩护,但这两个原则直接应用于非刑事活动本身就颇具争议。且当前《出口管理条例》规则不加区分,这些针对美国公民的规定,并非以符合这两个原则的方式实施,其合理性难以立足。 这一不合理的管辖权扩张,严重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与正常交流。
本文英文原文为《Mapping Export Control Extrat-erritoriality in the US-China Technology Decou-pling》,发表于《Journal of World Trade》58卷第4期。
参考资料及数据来源
[1]Christopher Donovan,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1979: Refining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Machinery, 4(1) Boston College Int’l&Comp. L. Rev.77, at79–82(1981).
[2]Oliver Hailes, Lithium International Law: Trade, Investment, and the Pursuit of Supply Chain Justice, 25(1) J. Int’l Econ. L. 148, at 158–60 (2022), doi: 10.1093/jiel/jgac002.
[3]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Policy: 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CoCom) in Technology and East-West Trade 153–170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79), https://www.princeton.edu/~ota/ disk3/1979/7918/791810.PDF (accessed 12 May 2024).
[4]Chad Brown, Export Controls: America’s Other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export-controls-americasother-national-security-threat (accessed 12 May 2024).
[5]List of Dual-Use Goods and Technologies and Munitions List,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s and Technologies (5 Dec.2019),https://www.wassenaar.org/app/uploads/2019/12/WA-DOC-19-PUB-002-Public-Docs-Vol-II-2019-Listof-DU-Goods-and-Technologies-and-Munitions-List-Dec-19.pdf.
[6]Joop Voetelink,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US Export Control Law. The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s, 1(1) J. Strategic Trade Control 2 (2023), doi: 10.25518/2952-7597.57.
[7]Gregory Bowman, A Prescription for Curing U.S. Export Controls, 97(3) Marq. L. Rev. 599, 615 (2014), doi: 10.2139/ssrn.2227777.
本文作者
商舒,环仲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执业律师。曾担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调解和在线争议解决部门负责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英美法项目主要负责人;发表过多篇英文学术论文,在美国国际法学会、硅谷仲裁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任职,同时在中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仲裁委员会电子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电子仲裁中心、美国国家仲裁中心、等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有丰富的仲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