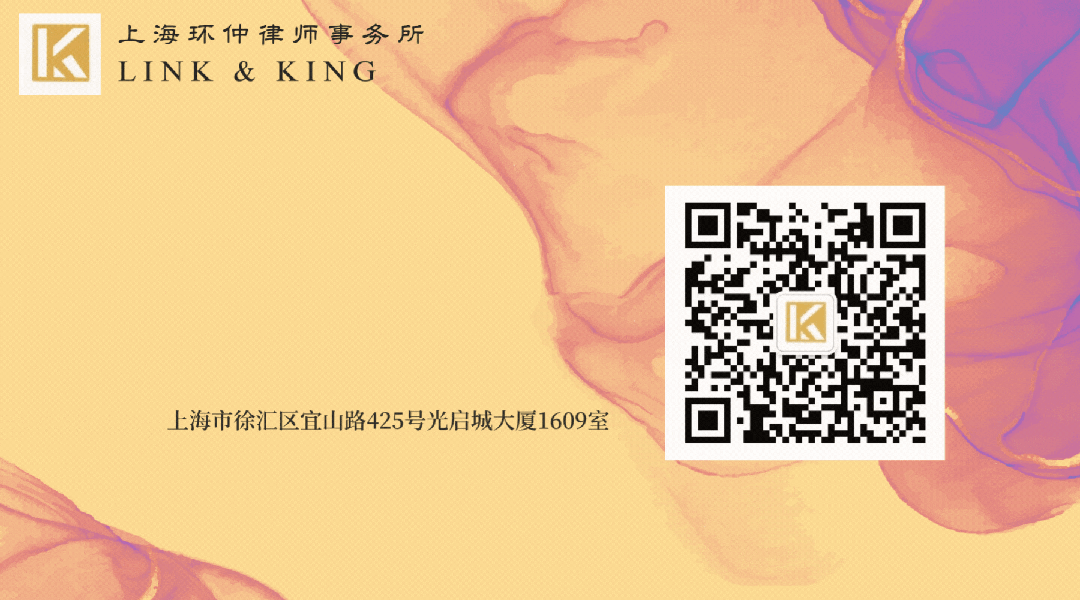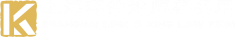香港法院:当事人拖延仲裁庭临时措施审理,法院可提供司法救济
编者按
香港高等法院陈美兰法官在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领域作出了诸多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意义的判决,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具有重要价值。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香港高等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方面的观点,以及把握国际仲裁普遍秉持的理念与实践取向,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国际仲裁团队在袁杜娟律师的带领下,将分期推出陈美兰法官的重要案例及相关评析。我们希望借此搭建一个专业的平台,为法律实务界与学术研究者提供高质量的参考与启发。 前言 2024 年 12 月,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就 Company A and Company B v Company C [2024] HKCFI 3505 案作出裁决,陈美兰法官(Mimmie Chan J)指出:若仲裁庭有意作出临时措施,但一方长期阻挠、拖延相关条款审理且拒不遵从仲裁庭指令,导致临时措施迟迟未能落地,法院可提前签发禁令,以辅助仲裁程序推进并保障当事方权益。香港法院重申,其依据《仲裁条例》第 45 条准予临时措施的宗旨,在于为仲裁程序提供便利与协助。同时明确表态,对蓄意拖延、执意阻碍仲裁进程的行为持坚决反对(绝不纵容)的态度。 本文将从案件事实与程序脉络、核心争议焦点及香港高等法院裁判依据等维度,对该判决展开剖析与探讨。 程序背景 本案争议源于和解协议,协议中C公司承诺支持B公司首次公开募股。A、B公司主张C 公司违反该和解协议,遂向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争议解决中心提仲裁,索赔约5500万美元;C公司亦反索赔约 200 万美元。 仲裁期间,C公司全资子公司SZ在沪市公告,称C公司将转移现有业务与资产至SZ及关联方。A、B公司认为此举系恶意剥离资产,致未来仲裁裁决无法执行,遂于2024年5月3 日向仲裁庭申请紧急临时救济,要求禁止资产转移及 C 公司存 55,506,138.62 美元至托管账户(下称 “托管救济”)。 仲裁庭未即时采取措施,但允许A、B公司向香港法院求紧急救济。5 月 24 日,A、B 公司提单方面禁令申请,法院当日批临时禁令,有效期至 5 月 31 日双方聆讯。5 月 27 日,A、B公司再以原诉传票向香港高院申请禁令,内容与仲裁申请基本一致,禁止C公司转移资产。5月31日,C公司向法院承诺:不转移资产至SZ及关联方,仲裁庭就紧急救济作决定前,不从香港转移限额资产。 仲裁程序同步推进:2024年5月28日,仲裁庭表示或准初步禁令,邀双方提交草拟命令与反对意见,但双方就托管救济条款始终未达成一致。后续仲裁庭多次发程序令推进: 6月14日第32号令:裁定有权禁资产处置,要求双方协商托管条款并报结果; 7月11日第35号令:要求协商 “日常业务开支” 等,明确托管协议应含存5500万美元资产、SZ 存资产等条款; 8月19日第36号令:要求C公司存 22,585,456.19 美元现金,预留日常与法律开支,现金不足则 SZ 补差额; 9月11日第37号令:明确C公司承诺及此前义务,需达成托管协议且仲裁庭认定后方算履行; 10月7日第41号令:修改SZ支付责任,要求 C 公司两周内存入全部资产,限双方一周内协商完剩余条款,未果则仲裁庭定条款。 法律原则 A、B 公司申请法院禁令的法律依据为《仲裁条例》(第 609 章)第 45 条,相关条款内容如下: 第 45 (2) 条:“原讼法庭可应任一方申请,就已在或拟在香港内外开展的仲裁程序,核发临时措施。” 第 45 (4) 条:“原讼法庭可基于以下理由,拒绝依第 (2) 款核发临时措施 ——(a) 所涉临时措施当前属仲裁程序标的;(b) 原讼法庭认为,由仲裁庭处理该临时措施更为适宜。” 第 45 (7) 条:“原讼法庭依第 (2) 款对境外仲裁程序行使权力时,须考虑以下事实 ——(a) 该权力附属于境外仲裁程序;(b) 该权力旨在为境外对仲裁程序有基本司法管辖权的法院或仲裁庭的程序提供便利。” C 公司针对原诉传票提出两项抗辩意见,此即本案争议焦点:其一,本案仲裁庭已在仲裁程序中,通过第 36 号、第 41 号程序令,准予 A、B 公司所寻临时措施,故本次向香港法庭的申请已无必要;其二,香港法庭应依《仲裁条例》第 45 (4) 条拒绝核发临时措施,因本案中 A、B 公司所寻临时措施显然属当前仲裁程序标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满足第 45 (4)(b) 条要求,即由仲裁庭处理该临时措施是否更为适宜。C 公司主张,由香港法庭处理相关事宜既不合适,亦不符合香港法庭核发临时措施时应考量的公平、便利等条件。 裁判依据 香港法庭审理后认定,因仲裁庭尚未作出临时措施最终决定,双方也未敲定托管协议条款并获仲裁庭确认,故仲裁庭并未准予临时措施,C 公司第一项抗辩不成立。 法庭进一步指出,即便假设仲裁庭已准予临时救济,本案中法庭核发禁令仍属适当,理由为:依据《仲裁条例》第 45 (7) 条,香港法院行使核发临时措施的权力,旨在为境外仲裁庭程序提供便利,推动争议通过仲裁公正快速解决。本案中,虽仲裁庭自 2024 年 6 月发第 32 号程序令至庭审已超 4 个月,但仲裁庭要求双方协商落实托管协议的指令未被遵从,且 C 公司未遵守该指令。鉴于 C 公司拖延协商、阻碍托管协议签订且不遵仲裁庭指示,法庭应行使权力,以实现《仲裁条例》及第 45 条的立法目的与宗旨。陈法官明确表示:“依我之判断,无论如何,任何法庭都不应纵容被告的此类拖延行为及不遵守指令的行为。因为根据《仲裁条例》第 3 (1) 条,该条例的目的与宗旨是让法庭为通过仲裁公正、迅速地解决争议提供便利,且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同时,第 45 条亦明确规定,法庭作出临时措施命令的权力,其目的在于为仲裁庭的程序提供便利。”(强调为作者后加) 此外,即便假设仲裁庭已通过相关程序令准予临时救济,原讼法庭仍有权依《仲裁条例》第 61 条强制执行该临时救济措施。但考虑到 C 公司对遵循仲裁庭命令持阻挠、不配合态度,仅强制执行仲裁庭程序令,不足以给 A、B 公司充分保护。因此香港法庭认为,按原诉传票请求核发禁令,在仲裁庭作出最终命令或裁决前维持现状,才属适当、公正且便利。 典型意义 本案中,香港法院重申依《仲裁条例》第 45 条核发临时措施的目的,即旨在为仲裁程序提供便利与协助。同时,陈美兰法官的裁判亦明确,法庭对蓄意拖延、执意阻碍仲裁进程的行为持反对(绝不纵容)态度。 因此,若仲裁程序中任一方存在拖延、不配合、阻挠等情形,即便仲裁庭即将或已发出临时救济,也不影响香港法庭依同款条款核发临时措施。 此外,本案判决还体现出,香港法庭支持并便利仲裁的政策倾向,不仅表现为司法机构尊重仲裁程序与仲裁庭决定、尽量减少干预;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当仲裁程序遭不当阻碍时,法庭会主动行动,为仲裁庭及当事方提供司法救济。 环仲点评 该案判决对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案明确了《仲裁条例》第45条的适用边界:法院在仲裁程序未能及时提供有效保护,或一方当事人故意拖延、阻挠仲裁庭临时措施的落实时,可以主动介入,提前给予禁令。这一做法凸显了香港法院“协助而非取代”仲裁庭的功能定位,即司法机关并非要削弱仲裁庭的权威,而是通过司法救济弥补仲裁机制在执行力与时效性方面的不足。 判决传递了对“拖延战术”的零容忍态度。仲裁的价值在于快速、公正地解决争议,但若一方当事人通过程序性对抗长期阻碍仲裁庭指令的落实,则不仅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削弱仲裁机制本身的公信力。陈美兰法官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法院不会纵容此类行为,这对于规范仲裁参与者的诉讼行为、维护仲裁程序的严肃性具有积极意义。 该判决展示了香港法院在国际仲裁司法协助中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态度。即便仲裁庭已作出一定的程序性命令,若当事方拒绝配合,法院仍可依据《仲裁条例》第61条和第45条提供进一步保护,避免单纯依赖仲裁庭命令而导致当事人权益无法有效保障。这不仅增强了仲裁的可执行性,也提升了当事人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的信心。 综上,本案体现了香港法院在坚持仲裁自治原则的同时,能够在必要时果断介入,提供及时且有效的司法支持。这一平衡既巩固了香港“仲裁友好司法辖区”的声誉,也为未来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范式。对于企业而言,本案提醒其在仲裁中应善意履行协商义务,否则可能面临法院直接介入并作出不利禁令的后果。 案例来源: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 判决原文: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loadPdf.jsp?url=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word/vetted/other/en/2024/HCCT000060A_2024.doc&mobile=N 环仲仲裁业务团队 袁杜娟 环仲高级合伙人 商舒 环仲高级法律顾问 陈珏 环仲高级合伙人 汪峻岭 环仲高级合伙人 涉商事纠纷相关业务咨询请点击阅读原文,直达环仲官网,或电话咨询:18616775507,邮箱咨询:judy.yuan@linkarb.com.cn 本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资讯或文章仅为交流讨论目的,不代表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法律意见。任何依据本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作出的判断或决定(无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您需要相关法律意见或法律服务,欢迎与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联系。 点击“阅读原文”可访问律所官网